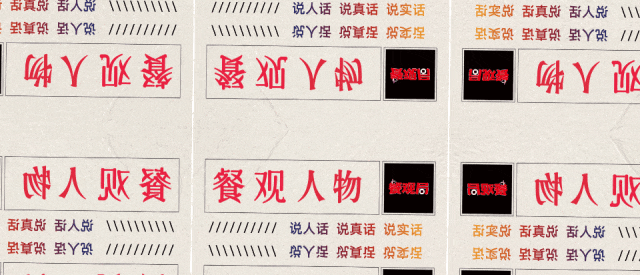「每一次归零
都意味着再一次出发」
他,没上过一天学,13岁离家出走流浪,被坏人骗去乞讨;
他,20岁创业失败,负债累累,冒危险下煤矿赚钱还债,出事故被砸成骨裂;
他,屡败屡战,好不容易接近成功,却因一场意外,一夜归零;
他,在拉面馆打工遇到著名导演,引荐到北京做私厨,从一无所有到品牌估值过两亿。
……
这些离奇经历,每一段都如同戏剧桥段,但却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。这是北京高端清真私房菜“醺季”创始人马天明的真实故事。
马天明,1986年出生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的一个山村里。自小因家庭变故,虽渴望学习,却未能走进校门。
1999年,13岁的马天明毅然离家出走流浪,却不慎被坏人骗进“丐帮”,被勒令乞讨。逃出魔掌后,马天明一路打工,学会拉面的手艺谋生,从此与餐饮结下不解之缘。
此后,马天明不断打工攒钱创业做餐饮,他开过拉面馆,承包过大学食堂,做过中餐厅,卖过火锅底料,但均以失败收场。马天明甚至忘记自己失败过多少次——他曾搏命下矿井赚钱还债,也曾几乎身无分文从新疆骑行到内蒙。认知和管理上的欠缺,让他在创业时踩了无数的坑。
但马天明失败后从不气馁,摔倒后就爬起来,从头再来。他屡败屡战,终于摸索到餐饮创业的正确方向。如今,马天明在北京的两家“醺季”院子,生意红火,拥有大批忠实客户,常居北京市大众点评排行榜前排,品牌估值2.2亿。
餐饮是个充满想象力的行业。有草根起家的餐饮人,把拉面馆、饺子铺这些不起眼的小买卖干成大连锁、大品牌;也有开局就含“金汤匙”的老板,手握丰厚资本,却把大酒楼、大连锁做到负债累累、亏损连连。决定这一切的,与创始人最初的资源、资本、人脉、权势无关,而是与创始人的魄力、性格、价值观、为人处事有关。
马天明虽未上过一天学,但他用过往验证了“真正的天才都极具信念”——有极致化的追求和坚持,即便面临艰难险阻,也要燃烧一把。唯有不屈服命运,奋力抗争,才能扛过每一次的打击与困境。创业不易,这种不畏惧失败的信念感,在餐饮行业进入迷茫期的当下,显得格外珍贵。
以下,是这个餐饮老板的故事。

图|受访者供图
01从流浪少年到餐饮学徒
第一次离家出走是11岁。出生在甘肃山村里的马天明,自小因家庭变故,受尽同龄人欺辱,和家人的矛盾也日渐严重,逃离的念头在他心中越扎越深。
但第一次出走隔天就被村里人碰到带回了家。第二次,马天明13岁,制定了更周密的出逃计划,他去了兰州安宁区,地处黄河北,比较偏僻,遇见老家熟人的概率也比较低。
虽然马天明揣了30块钱,但由于年纪太小又不识字,没有勇气开口求职,被迫开启了流浪之旅。饿了就买点干粮吃,累了就找个桥洞睡觉,直到钱花没了,肚子也饿得“咕咕”直叫。
坏人发现了独自流浪的马天明,给他买了衣服和食物。刚离开山沟不久的马天明,对外界的认知还很懵懂,对社会的险恶也全然不了解,以为对方是好人,跟着就走了。
对方带他和其余被骗来的十几个孩子回到郊区的一座厂房。每天凌晨五点,一辆黄色面包车塞满小孩,从郊区出发,把孩子们放到不同的地方乞讨。
马天明这才发现不对劲——对方会给孩子们派发任务,从开始的规定每天乞讨30块钱,慢慢增加到50、100、200甚至500块钱,完不成任务就吊起来用皮带抽打。有小孩试图逃跑,抓回来就会被打断腿,落下残疾。
马天明在“丐帮”呆了两三个月,最开始在郊区,后来对方见他听话,把他送进市区乞讨。马天明留了个心眼,他逐渐打听到火车站的方向,试探了几次路线,记住几条小路。一次在距离火车站几百米处乞讨时,直接甩开对方跑上了火车,跟在其他乘客屁股后面逃过了检票。
火车上,查票的列车员走过来,他就钻进火车座椅下面躲起来。一直到列车抵达终点,才发现这趟车的目的地是上海。
身无分文的马天明在上海下了车。由于是东乡族,马天明只能吃清真食物,想在上海找清真饭馆打工,但没人愿意录用他。流浪几天,粒米未进,实在是饿急了,马天明鼓起勇气走进南京路的一家清真饭馆,点了几个便宜的小菜狼吞虎咽吃起来。
饭毕,一个穿西装的人走过来,“他要是打我该咋办?”马天明心里害怕,脑袋里冒出很多想法,急得哭了起来——“我是从兰州偷跑来上海的,兜里没钱,我在这打工行不行?”
对方并未责怪他。刚巧,这个老板也是甘肃人,他告诉马天明,这里用不了童工,会被举报,你去找小拉面馆,肯定会要你。对方不仅没收钱,还给马天明指了几家店,马天明去了其中一家拉面馆,老板夫妻是青海人,把他收下了,一个月工资80块钱。
当时上海正常的服务员工资是300块钱,但80块对13岁的马天明已然是一笔巨款。干了三个多月,拉面馆转让了,马天明拿着打工赚到的钱买了些水果,去收留他吃“霸王餐”的那家饭馆结账,但对方没要他的钱。
马天明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友善,也为他此后的重情重义埋下伏笔——马天明后来创业的餐饮品牌“醺季”,兰州话谐音是“兄弟”,他借此感恩一路走来遇到的贵人。
千禧年的上海很繁华,但对一个必须饮食清真、还是童工身份的孩子来说,生存太艰难。马天明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兰州。但上海短暂的四个月,让马天明找到了方向:学一门手艺,自己开个餐馆。此后,马天明的人生与餐饮行业紧密绑定。
回兰州后,马天明找了一家拉面馆打工,一年多的时间学会了基础的切面、揉面。后来经人介绍,去了一家本土拉面行业比较头部的餐厅,能学到很多,工资也比之前高,算上奖金能拿四五百块钱。干了两年多,马天明出师了,基本什么面都会做,拉面也成了他傍身的手艺。
当年离家流浪时,他心里对家人是有怨恨的,但漂泊太久,这些恨意已经烟消云散,变得不重要了,毕竟未来人生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。
18岁,马天明离家出走后,第一次归家。这是他对前18年的自己做的一次告别,也是未来人生的重新出发。
02第一次创业失败,下煤矿还债
朋友给马天明介绍了一份工作,在吉林长春的一家高端饭店做拉面师傅。长春呆了一年,虽然比兰州挣得多,但很辛苦。看着这几年攒下的积蓄,马天明萌生出“自己干”的念头。
刚巧,一个表弟在内蒙呼和浩特的工地上做劳务输出,彼时呼市正在大开发,马天明认为过去开个拉面馆一定有生意。
马天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,跟表弟合伙。租下来的店面没有液化气,连正经的灶台都没有,马天明亲自上手,用砖头和泥垒了一个土灶。房租、装修、买东西,前期投入成本一共花了16万,马天明出了6万。
“看别人的生意干得挺好,自己做起来,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”马天明对餐观局感慨道,“做生意不是有门手艺就行的。”由于各方面经验都不足,拉面馆才营业半年,就以失败收场,分到马天明身上的债务高达8万多块钱。
继续回餐馆打工,猴年马月才能将债还清?马天明决定跟着村里人下煤矿,一个月能挣四五千。这是个拿命赌钱的活计——矿井极深,主矿井斜着下去,最远的要下20多公里,矿车也要坐十几分钟。那个年代的防护也不够先进,经常有矿工出事故被抬上来,血肉模糊。
马天明虽然害怕,但没退缩过,咬着牙也要下矿。每天从井下回来,全身都是黑的,只有牙齿是白的。为了多挣点钱,其他人是8小时制,马天明直接干16小时,两班轮换的时候,他干脆就不上地面了。
玩命干了一年多,终于把帐还清了。马天明琢磨着,还完债,再下一年矿,挣个10万块钱,再开个店。
为什么那么想做生意?——“从小在村里面,就是一个任人欺负的孩子,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想证明自己。”马天明说。即便是下煤矿挣辛苦钱,他也要咬牙攒钱创业。但世事难料,马天明的胳膊在矿下因事故被砸成骨裂,失去了下矿的资格,只能拿一万多块钱的赔偿回家养伤。
养了没多久,2008年,马天明又去了新疆,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餐饮店做管理。
“那个店主打火锅,一共七层,一层只卖拉面,其余六层都是火锅。”马天明感慨道,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火锅,也是第一次接触餐饮管理。”虽然只管理拉面这一层,但对马天明来说已经是餐饮能力的升级。
干了一年多,马天明的工资从1800块钱涨到3000块钱,算是当地不错的收入。在马天明憧憬着攒够钱再次创业时,所在处发生意外。他只能回到兰州,一切再次归零。

图|受访者供图
03“创业屡战屡败”
出身草根、从未上过学,13岁就开始流浪,马天明在认知上的欠缺需要格外努力,才能和普通人在同一起跑线。
这种欠缺让他在创业上屡次栽跟头,但每一次踩坑都更快让他形成新的经验认知。正所谓勤能补拙、跬步千里。
从新疆回到兰州时,马天明的妹妹刚巧要去内蒙古通辽上大学,送妹妹去学校后,马天明又萌生一个念头——在大学里开一家清真食堂怎么样?他说干就干,再次去了长春,和朋友在东北师范大学食堂里合伙承包了一个档口。
这次创业,马天明任意发挥自己的创新性,只炒面就能炒出七八十个品种,整个档口的墙面上全是菜单,每天他都能变着花样新增几个菜,几乎学生点什么他都能做出来。
但这种创新也让马天明栽了跟头。学生一人点一个菜,不仅做起来麻烦,总账算下来根本不赚钱——其一,备菜多,炒菜久,时间成本高;其二,学校要求必须卖得便宜,但却没有相应的补贴。做了两年,马天明一算,自己基本上不赚不赔。
这也让马天明对餐饮创业产生了更深的认知:要先学会算账,再琢磨创新。
档口转手以后,马天明回到兰州,再次从头开始。说来也巧,马天明每次回到兰州,都意味着一次事业的归零,也意味着一次重新出发。
马天明在餐饮创业上屡战屡败,但越战越勇。不安分的血液又在体内叫嚣,他这次决定依仗在新疆做餐饮的经验,在老家邻县跟朋友合伙开一家大盘鸡。
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面,最后盘下来的是一个500平米的房子,“这么大的餐厅,做大盘鸡是不是有点可惜?”马天明跟朋友一合计,拍板改成做中餐厅。
但彼时马天明对中餐不是很懂。他通过朋友,从兰州请了厨师长,对方带了一个团队过来。但在后来的磨合中,由于马天明与合伙人的年龄都比较小,总是在管理上被厨师们压一头。厨师团队工资高不说,食材方面浪费也很严重,成本极高。
餐厅投入了40多万开的,结果半年以后查账,又亏损了接近50万。
“中餐不赚钱,怎么办?要不转型成火锅吧,至少不会受制于厨师,”马天明想。这次他不敢贸然直接转型,而是试着加了火锅的品类,结果大受欢迎——最后中餐一桌都订不出去,店里全是吃火锅的。马天明与几个合伙人商量了一下,决定把中餐撤掉,全力转型做火锅,厨师班子也换了一批。
此时,马天明系统认识了管理、财务上的问题,还有选定品类、测品的重要性,餐饮生意走上了正轨。他对未来预期极好,不仅贷款跟朋友合伙开宾馆,还在老家又开了一家火锅店。
然而天不遂人愿,在一切向好发展时,意外再次降临。马天明不得不关了经营良好的餐厅,偿还银行贷款后,再次一无所有。

图|受访者供图
04戈壁滩上的救赎
三次创业、三次失败,以及无数次的从零开始,一向越挫越勇的马天明突然失去了方向,他变得疲惫又无所适从。彼时的他才28岁,却仿佛经历了大几十年的人生。
他去了趟太原,又去了趟东北,紧接着是天津、青海、新疆,试图和老朋友们聊聊天,但仍然没能找到心灵上的救赎。
马天明决定来一次短暂地出逃。他买了辆二手的自行车,2015年的大年初八,从乌鲁木齐出发,沿着戈壁滩一路向东,希望在西北的风沙下重新寻找到自我。
戈壁滩的风很大,马天明时刻要与大风做抵抗,以免被刮走。路过一些放牧人的帐篷,对方会好心地送给他几个馕。幸运的时候,会在太阳落山之前碰见一些废弃的检查站,有些上了锁,马天明就从窗户爬进去,凑合休息一晚上。
晚上没有落脚地时,他不敢停下来休息,因为附近有狼在徘徊,只能硬着头皮向前骑。最绝望的时候,是晚上远远看见了前方有城镇的灯光,但用尽全力骑两三个小时也无法抵达。
骑了二十几天,路过酒泉、嘉峪关,一路到了张掖,又来到阿拉善。在阿拉善休整几天后,马天明骑到了甘肃金昌。
抵达金昌时,马天明身上仅有的盘缠都花光了。他在金昌本地找了一家饭馆,打了50天的工,做拉面,意外认识了未来的岳父。“这个人在金昌当地威望很高,孩子也都比较有出息。尤其是三女儿,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,毕业后在北京工作。”餐馆的老板对马天明介绍道。马天明只当故事听,他从未想过,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去北京谋生,更想不到故事中的女孩会成为自己未来的另一半。
从金昌离开,马天明骑去了青海,又路过宁夏银川,最后抵达呼市,在包头落了脚。这一路,马天明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,那些人生轨迹中的大起大落,也许是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没有本钱的马天明,在包头找了一家餐厅打工,由于已经在餐饮上积攒了颇多经验,没多久,餐厅的流水就在马天明的管理下水涨船高。一年后,马天明辞职去了银川。
彼时银川流行“火吧”——就是又能唱歌、又能吃火锅的店,仅一个吴忠市里就有上百家火吧。马天明的思维又活络起来:如果给这些火吧供应火锅底料,能不能赚钱?
但他只考察了火吧的市场,没有考察火锅底料市场,清真的火锅底料在当时已经有颇多知名品牌。马天明自认为开过火锅店,有炒底料的经验,他在乡镇里找了一座院子,打造成厂房,亲自上阵炒底料。在包头打工攒下的十几万块钱,全部投进第四次创业里,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了。
回到包头,原来打工餐馆的老板又开了一家拉面馆,马天明决定留在包头帮忙。
2017年,王小帅执导的电影《地久天长》剧组来包头拍摄,刚好住在马天明所在的拉面馆楼上的宾馆。后来,王景春、咏梅凭借这部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银熊奖,《地久天长》也因此留名影史。
拍摄时,剧组几乎每天晚上都来馆子里吃面、吃烧烤,有时候吃完饭忘记给钱,马天明也不急着要。渐渐,马天明和剧组建立了信任关系,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,因缘际会有了交集。
后来,剧组又去了福建拍摄,但马天明依旧和王小帅导演保持着联络。当年11月,马天明和几个朋友在包头合伙开了火锅店,给王小帅导演打了电话,没想到王小帅把剧组的核心演员们都带来捧场。
高汤滩羊火锅让大家赞不绝口。王景春开玩笑道,“小马,我在上海有几家火锅店,你跟我去上海开店吧。”王小帅紧接着说,“小马,你来北京,北京市场大。”
马天明无比兴奋,“北京市场大”,这几个字深深烙印在他脑海里。两个月后,马天明真去了北京考察市场,王小帅把他们一行人带到聚宝源,门口排队的人让马天明惊呆了——“在包头没见过这场面,门口全是人在排号。我们一顿饭没吃完,隔壁桌已经翻台四五次了。”
“我要留在北京。”马天明在心里暗自发誓。十三岁时,繁华的上海让他胆怯,此后马天明一直在甘肃、东北、内蒙和新疆几地徘徊,不敢再去一线城市打拼。但这次,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拼一把。

图|受访者供图
05高端清真火锅的诞生
考察几个月后,几个合伙人认为北京餐饮水太深,不敢做,只有马天明坚持留了下来。他把西北的生意做了切割,自己只拿了两万多块钱留在北京,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。
一次,王小帅导演的家人过生日,想在密云水库来一次野外聚餐,无奈不知道该吃什么。马天明自告奋勇,“我来!”他从包头和银川运了几只羊,一个人做完了100多个人的餐。
许多在场的明星都加了他微信,想邀请马天明帮忙做上门家宴。
但马天明没有接触过家宴私厨这一行,甚至没有厨房、没有帮手,好在导演将工作室的厨房借给马天明用于加工食材。一个人提前几天去备菜,羊又是从西北运来北京的,该如何定价?
一个演员给他下了第一单,做二十几个人的家宴,马天明报了个价格,“那就给3000块钱吧。”对方觉得太便宜,让他加价,马天明坚持只收3000。做了几次家宴后,马天明的名声在娱乐圈打响,但他的价格涨幅却不高,去掉成本也剩不了多少钱。艺术家刘晓东在一次上门家宴后帮他确定了价格:6888元。
马天明这才有了正式的价目表。就这样,马天明“一人、一羊、一锅走天下”的北京家宴生涯走上正轨。
手里有些积蓄后,马天明在酒仙桥租了一套商住的公寓,简单装修一下,客厅摆了一个12人桌,主卧摆了一个8人桌,正式做起了私房菜。但公寓隔音太差,总是被邻居举报,最终房东强行收回了房子。马天明干脆去草场地艺术村租了一个院子,滩里小院由此开启。
草场地的私厨院子不大,冬天只能接待三桌,而且只有晚上营业,主要做高汤火锅。但来院子的人却“非富即贵”——不少京城叫得出名字的明星大腕、投资大佬、企业家都来过。
马天明的自信也逐渐回归。自13岁流浪开始,到后面打工、创业,马天明一直在几地来回穿梭,没有一处落脚地让他持续呆两年以上,没有归属感。但在北京的私厨院子,他终于找到了自我价值所在。艺术家刘晓东老师曾告诉他,“小马,你要把你自己定位成艺术家,你就是艺术家,你不是厨师,你做出来的所有的东西,都是艺术。”这启蒙了马天明,他开始在菜品的质量、摆盘、服务和就餐环境上入手,致力于打造一家以食材为笔墨、以厨艺为韵律、以摆盘为色彩的高端私房菜。
疫情期间,由于种种原因,草场地的院子还是关掉了。但近两年的打磨和不断创新,让马天明提升了很多。再加上有幸结识了餐饮导师郭晓东,他对餐饮有了更加系统性的学习和了解,“原来餐饮还需要对研发、定位、选址各方面都有理解才行。”
在郭晓东的指导下,2021年醺季品牌诞生,随着首店醺季·丽都院子开出后,品牌稳扎稳打,一年一店,2022年鼓楼院子开业,2023年青年路院子面世。
马天明告诉餐观局,醺季的差异化在于对食材、环境和服务等细节的极致追求。“高汤羊鲜火锅,不同于老北京涮肉,在食材的选择上更加精细多样化,而且北京缺乏高端清真餐饮品牌。”马天明的目标,是将醺季打造成第一家进入“米其林”级别的清真餐饮。未来,还计划以北京为中心将高端清真餐饮版图扩展到其它一线城市。
“算没算过自己失败过多少次?一共赔了多少钱?”面对餐观局突如其来的问题,马天明愣了一瞬,随即又大笑起来:“真没统计过。因为失败过太多次了,每次跌倒了就爬起来。”
也许经历过的波折起伏太多,如今的马天明心态格外平缓。他认真道,“每次失败后我只有一个规划,就是哪怕打工一年,再挣点钱,我也要继续做我想做的事。但是成与不成,我没考虑过,只是单纯的想去做。”

图|受访者供图
如今醺季生意红火,常居北京市大众点评排行榜前排,品牌估值超过2亿。马天明也从当年出身贫困山村的流浪少年,变成京城颇有名气的清真餐饮老板。
不沉溺于痛苦,相信谋事在人,不向命运低头服输,这或许是每一个逆风翻盘的餐饮人最深刻的底色。
(Editor丨CaMedia)
*转发或引用须表明来源于餐观局,否则将追究侵权责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