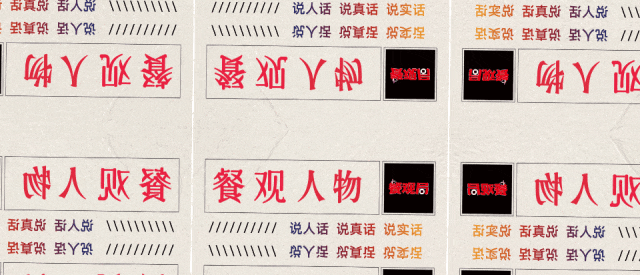「一次踩中是幸运
次次踩中是能力」
早上九点前,王一达准时出现在公司,没什么其他事情,他都会待在办公室。我们见到他时,他正坐在桌前,对照着一份砂锅店的菜单,在本子上振笔疾书——比起电脑,他更习惯将思维落在纸上。王一达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,因为频繁地翻动,笔记本的皮面已经摩擦到泛白。
在办公区南面的墙上,挂着长达数米的屏幕,上面排布着多家火锅门店的监控画面——分散在北京各处的“井格重庆火锅”,正是这家名为圣达餐饮的公司旗下的品牌。
最多的时候,井格拥有152家门店,覆盖几十个城市,在海底捞、呷哺呷哺、巴奴等品牌牢牢占据的火锅连锁市场撕开一道巨大裂缝。而王一达是这个火锅品牌的开创者。
在几乎人均“困难模式”开局的餐企老板群体中,王一达是鲜有的“幸运儿”:创业有人支持,从不为钱发愁;赶上微博的风口,自家火锅成为第一批网红店;第一个把火锅店开进商场,吃到商场餐饮的第一波红利;赶上团购大战,卖券卖到上亿规模……
某种程度上,王一达又没有完全被幸运眷顾。当年作为餐饮小白,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该如何经营一家餐厅。直到开店的第五年,他才第一次搞了个账本开始记账;到开店的第七年,在已经开出七八家分店的情况下,才注册起餐饮公司,尝试着公司化经营。
成功的经验是不断“踩坑”换来的,如他钟爱用纸张记录的习惯一般,亲自用手写过一遍,才能更好地迸发灵感。
尽管过程中起起落落,但王一达却始终坚信餐饮的力量。在他看来,餐饮永远是民生第一大行业,从宏观视角来看,不管经济是上行亦或下行,餐饮的持续增长是一定的,这个行业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。
同时,餐饮也在朝着专业化、连锁化不断发展。刚入行时,王一达认为餐饮就是“做个饭而已”,如今他对这行有了更多敬畏心——餐饮是一个复杂的行业,必须要用经营思维去建设。
如今,王一达的餐饮事业正在向多品类、多品牌发展,也正在筹备更具创新性和颠覆力的火锅店。

图|来自井格官网
01抛下铁饭碗,去北漂!
在北漂成为火锅店老板之前,王一达曾是重庆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。
出生于体育世家的王一达,十几岁就进了专业队,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。别人在上学,他天天就是比赛,甚至连高考都没参加。19岁时,王一达从职业队退役,转业到了重庆一个地方体育局,在体校带队当教练。
后来,22岁的王一达成为整个重庆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。在家人原本的规划下,王一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晋升,有一个不错的仕途。
但彼时的王一达年轻气盛,比起在体制内稳扎稳打的成长,他更渴望跳出当下的环境出去闯荡一番。恰逢那时初恋以失败结尾,在工作和感情的双重刺激下,王一达迫切想要逃离重庆,去做一番自己的大事业。
2004年,做主持人的姐姐圣爱从重庆卫视转到北京工作,撺掇着王一达陪她一起去北京,姐弟俩一拍即合。为了说服母亲,王一达花两百块钱造了一封北京体育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告诉母亲自己被录取了,要去脱产学习三年。母亲查阅过后,信以为真,便为王一达办理了停薪留职。
2005年2月,王一达如愿来到北京。起初,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姐夫帮忙找了一份工作,将王一达安排去做中介行业最基础的置业顾问。“那是人生中最苦的一年”,王一达回忆,“天天挤地铁挤公交,几乎转遍了全北京的大街小巷,每天都要走几万步。”好处则是,他对北京城有了快速的了解和认知,也为后来的餐饮创业提供了一些思路。
很快,谎称来京读书的事情败露了。得知真相后,母亲不断劝说王一达回重庆。“我坚决不回去。”
王一达更想在北京混出个模样。他想和姐夫做些房地产的项目,但姐姐对此持不同意见,夫妻俩还几度发生争吵。眼看两人为自己的事情争执不休,王一达决心要在北京另谋一份营生。
“我要开个正宗的重庆火锅。”王一达想。他自小爱好美食,但在北京的一年多,几乎没吃到好吃的店,更别提正宗的重庆火锅了。当时北京比较火的几家川渝火锅,在他看来都不地道。
为了筹备火锅店的启动资金,王一达把自己在重庆的一套小房子卖了,但还差一大截,他便又向姐姐求助。最终,圣爱补齐了剩下的钱,相当于与王一达合资,俩人各占50%的股份。在王一达眼中,姐姐圣爱是他最早的天使投资人。
就这样,2006年4月份,姐弟俩盘下了位于雍和宫附近的一家230平的铺子,门店装修成了重庆洞子火锅的样子。门脸三米宽,接着是一个25米的走廊,再往里空间便豁然了,来到火锅的主场:石桌子、宽板凳、大铁锅、九宫格......王一达原本起名“洞子火锅”,但工商注册没成功,便又依着门店的布设起了个“宽板凳老灶火锅”的名字。
北京第一家正宗的重庆火锅,也便由此诞生。

图|井格第一家门店
02“餐饮小白”,蒙眼乱干
彼时,王一达24岁,虽然成了火锅店的老板,但对于餐饮,对于经营,可谓是一窍不通。
这个年轻的“餐饮小白”没有获得新手光环加成,火锅店的生意不尽人意。不仅如此,王一达从“小天鹅”挖来的厨师长还干着吃供应商回扣的勾当,年轻气盛的王一达发现后,立刻和对方起了冲突。后来,王一达联系到重庆的老朋友刘继全。刘总手艺很好,在体校时,王一达天天吃他做的的蛋炒饭。
刘总熬制底料的方式完全按照重庆当地的做法,但这样的重麻重辣在北京市场多少有些水土不服。当时,火锅店只能勉强维持,每个月的营收有八九万块钱,但房租就有1万5,再刨除人工和其他成本开支,利润所剩无几。
到了2007年,情况更糟糕。为了迎接奥运,门店前的街道被翻修,处处乱七八糟。宽板凳迎来“生死局”,一天只能卖400块钱,完全维系不了正常的运转。
“熬不下去了。”王一达跑去找姐姐。他告诉姐姐,火锅店弄不下去了,现在还能以20多万的价格转让出去,正好平了欠酒水供应商的账。姐姐听完一言不发,只坐在那儿哭。王一达不敢继续提关店的事情,“得,不关,想想办法。”
第二天一大早,王一达飞回重庆,找来了做面点、盒饭的师傅。这就是他花费一整晚想出来的办法——既然火锅卖不了多少,那就扩充经营业态,卖盒饭,卖早饭。王一达第一次有了餐饮经营的概念。
王一达前后卖了四个月的早餐和一年多的盒饭。依靠早餐和盒饭的收入,火锅店得以继续维系。
彼时,王一达虽然整天在店里忙碌,却没有系统的经营理念,甚至连账都不记。当时还是收现金,钱每天“左兜进、右兜出”,对收入和支出压根儿没概念。
后来得益于明星们的微博宣传,宽板凳的生意一下火爆起来。到2013年,王一达已经开了8家店,宽板凳在京城餐饮圈也小有名气。然而,随着门店的快速扩张,问题很快也暴露出来。
当时,担任厨师长的刘总每天骑着摩托车穿梭往来于各个门店之间炒料、熬料。门店散布在北京城的诸多角落,簋街、双井、天通苑、石佛营……每一家都相隔甚远。一个月下来,刘总要骑五六千公里的摩托车,两只手上也满是炒料磨出的血泡。不但人辛苦,这样巡回炒出的底料味道也出现差异,各家店菜品出品也不统一。这对于连锁品牌是致命问题。
2013年11月份,王一达在东坝租了个地方,操办起来一个“中央厨房”,在这里集中熬制底料,并把毛肚、鸭肠等七八个卖得好的菜在这儿进行统一处理,再送往各个门店。“那时我们都说中央厨房,现在觉得是弄了个中央作坊。”王一达回忆。
“中央作坊”只存活了半年,就因没有资质被查处了。祸不单行,“宽板凳”也快要保不住了。团队开始注册商标,才发现为时已晚——“宽板凳”被人给抢注了。官司先后打了一年多,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这时,王一达还面临着要扩张到上海的抉择。如果继续以“宽板凳”的名字外扩,很容易带来一系列侵权问题。要解决这种情况,只有两个方案:第一,花500万把商标买过来;第二,换名字。
“什么玩意儿就500万?!”王一达一听,直接否了第一个方案。运动员出身的他带着一股倔劲儿:“来嘛,咬着牙硬刚,那就换。”就这样,2015年2月2日,北京二十几家“宽板凳老灶火锅”正式更名为“井格老灶火锅”。
不过,后来的几年,王一达也时常会反思,如果当时不心疼那500万,把“宽板凳”商标买过来,对于后面几年火锅店的经营或许大有裨益。团队后来测算过,那年的更名事件对火锅店后期的经营起码产生三成影响。

图|王一达和员工
03踩中风口,扶风而上
从2006年初入餐饮行业的小白,到如今对餐饮经营颇有心得的餐企老板,王一达经过了诸多风浪洗礼和历练。正可谓“英雄亦适时”,除了自身磨砺,王一达的创业路上还精准抓住了几个重要的时代风口:微博KOL、进商场、做团购……“宽板凳”和“井格”才有机会扶风而上。
2011年,新浪微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,明星们纷纷入驻,一条简短的微博就可以掀起一阵备受粉丝追捧的潮流。姐姐圣爱虽然早已退圈,但却有一群关系很好的圈内好友,比如谢娜、钱枫、谷智鑫等。
随着明星朋友们的微博宣传,宽板凳老灶火锅从不温不火,一跃成为北京最火爆的火锅店之一。2011年9月,宽板凳的营业额做到了史无前例的60万,王一达被吓到了:“60万的营业额是什么概念,一个月能挣将近20万!”等到同年冬天,宽板凳的营业额迅速做到上百万。王一达清楚记得,当时火锅店早上11点开门便大排长队,,一直到晚上11点都没停过。宽板凳的排队人群甚至影响到了街道正常的交通,惹得街坊打电话报警。
仅5个月的时间,宽板凳便净赚了300万。
趁着热度,王一达有了做大规模、开分店的想法。当年,离门店不远的簋街是北京美食中心,也是王一达心中北京川菜的殿堂,“当时做梦都想进簋街。”他对餐观局感慨道。赚到钱的王一达,终于有了把店开进簋街的能力。次年3月,宽板凳簋街店开业,一开业月营业额就做到了百万。很快,第三家店也开业了,这家店投资50多万,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回本了。
到这时,宽板凳已经颇具规模,经营也逐渐步入正轨。正好身边的明星朋友有意,王一达和姐姐商量,便开始引入外部股东,采用合伙制,谢娜、钱枫也都在那时成了宽板凳的单店股东。
2014年,宽板凳又抓住一个时代机遇。
当时,位于北京东二环的悠唐购物中心邀请王一达将宽板凳开进商场,采用合伙制的模式,共同打造宽板凳老灶火锅的商场店。在此之前,还没有火锅店开进商场的先例,尽管有些犹豫,王一达还是答应了。
悠唐给了宽板凳一家700平米的门店。在门店装修上,宽板凳也一改往日街边“野摊儿”的形象,开始向商场的规范化靠拢,有了正规的视觉设计、空间设计。最终,宽板凳悠唐店一共筹备投入400万,成为当时第一家进MALL的火锅店。
商场源源不断的客流持续为宽板凳造血,开业第一个月,营业额就达到了300万。“我从来没见过一天能卖10万块钱的。”王一达咋舌,他真切感受到了商场餐饮的巨大能量。
“进悠唐后,宽板凳的单店模型就已经发生了变化,以前走的是‘夫妻店’模式,后来就成了商场连锁餐饮。”王一达复盘道。
尝过时代红利的王一达,对创新业态格外关注。2015年,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前夕,二者为争夺市场打得“难舍难分”——王一达看到的却是这其中的巨大机遇。更名后的“井格”积极拥抱团购,依托平台助力,井格火锅成为当时整个北京火锅圈子卖券第一名,20多家店一年卖出去数亿团购券。其中,只美团一方给的预付款就有8000万。
巨大的现金流握在手里,王一达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。很快,井格的门店开到80多家,并且有6家店陆续在上海落地。
2016年,井格开放加盟,同时开始投建供应链,火锅底料的熬制由中央厨房转至工厂,向餐饮工业化进一步靠拢。到2019年,井格已经开出了47家直营店,100家加盟店,营收做到了12.5亿的规模,也曾一度准备上市。

图|来自井格官网
04用经营思维去干餐饮
宽板凳和井格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,作为掌舵者的王一达,也从“野蛮生长”的个体户思维转变成专业经营的餐饮企业家思维。
“一个长期主义的连锁品牌,需要规模化、专业化的经营建设。”意识到这一点后,王一达报了很多班,到处上课、学习。通过与很多专业人士的交流,王一达知道了企业组织架构的重要性。
随着门店不断扩张,公司也日益壮大。2015年底,王一达花费200万请来了逸马团队做连锁内部咨询。三位咨询师在公司入驻一年,从最顶层的企业文化开始梳理,到使命愿景、价值观,再到组织架构,乃至于各个部门的SOP(标准作业程序)手册。专业团队帮助井格建立起高效的组织架构和标准化作业程序,这也为井格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复盘自己的发展之路,王一达深觉比大多数餐企老板要幸运,“命好一些。”他开玩笑道。体育世家出身,自小家庭条件优渥,所以对钱不会格外看重。也正是这种对钱无所谓的态度,恰恰能让他在面临某些决策的时候,可以打开格局,不会因为钱的问题束手束脚。比如后期花费上亿投建的工厂,如今已经成为王一达口中的“养老”项目。
疫情前两年,王一达很迷茫,但到了第三年,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,开始思考餐饮事业的新方向。2022年,圣达餐饮由单一品牌化变成了多品牌运作,主打江湖菜的“耙耳朵”品牌诞生,2023年,美蛙火锅“蛙自由”在北京开出了第一家店。目前,王一达正在筹备的“砂锅婆”也即将落地。
“品牌的寿命是有周期的,总要去找挖掘第二增长曲线。”王一达表示。最近一年多,王一达还组建起技术团队,开始做一些研发。
做了十几年餐饮,了解越深,王一达越能体验到这个行业的魅力,对餐饮也多了几分敬畏和思考。他相信餐饮市场巨大的成长性,以及消费者消费需求升级所带来的增长空间。
最近,他还想通了一个问题——为何如今看来,井格的定位有些尴尬?因为井格做的是川渝火锅,是特色餐饮,但特色餐饮不具备大连锁属性。而海底捞、巴奴,是麻辣火锅,有家庭聚餐的属性,更为大众化,与商场消费者的调性更加契合的。特色餐饮的客群,更愿意去街边,而非购物中心。
王一达也是后来跟同行聊天时才恍然明白,自己这是在购物中心卖特色餐饮啊。“当时还在得意跟海底捞有差异化,真是要命!”
意识到这点后,王一达就开始筹划起新版本的火锅店。“重新做VI(视觉设计),商标、logo全变。”很快,新的井格品牌将与大众见面。
新品牌能否在海底捞、巴奴等火锅品牌的夹缝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,仍尚未可知。但王一达是乐观的,虽然重庆火锅是他身上最早的标签,但随着餐饮市场环境和消费群体的变化,品牌一成不变只会被时代甩在身后。
属于王一达的火锅创业故事,仍在继续。
(Editor丨CaMedia)